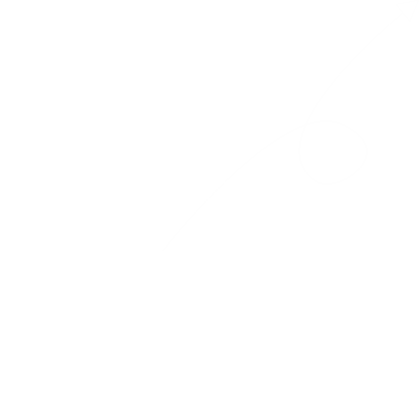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在你们‘城里人’看来‘是净土’,在我们‘村里人’看来‘净是土’。”
前几天,有平台发布了今年十大流行语,其中之一就是“数字游民”——无固定办公场所、依托信息技术远程办公,可自由流动的年轻群体。
时代飞速变迁,新群体出现并非新鲜事。但这类人群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的工作生活方式,还和具体的空间产生高度关联。稍加关注会发现,一些数字游民喜欢往乡村“游”,一些乡村也建立起数字游民基地或社区。如一条鱼进入水中,一些深层的张力也被“游”了出来:为什么到乡村去?如今的乡村如何与年轻群体互动?数字游民和数字乡村发展诉求间能互相带来什么?
因此,本文不是对一个新群体的简单描述,而是站在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到当下的时刻,去思考一个年轻群体和一个广袤场域是如何有效碰撞的。为了体现这些张力,本文选择了几组意象,并希望这些意象激发更多可能性,关乎生活的,关乎共存的,甚至关乎价值重构和道路选择的。
1980年5月,一封题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潘晓来信”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大讨论。有人称这场讨论为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40多年过去,精致利己主义者、单向度的人、小镇做题家等陆续被制造,内卷、悬浮、固化等困境不断出现,年轻人再度面对如何更好地生活的困惑。
仟一最近的工作,就在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第138号这间老房子里。此前的几年,她在广州做城市楼房的室内设计。为何来这里?“在城市做了很多案例,有点倦了。想通过建筑来看设计,城市太同质化了,反而农村有各样的建筑。”她说这话时,记者想起前一天在隔壁的墘头村,看到一棵大树从山洞样的民宿房间内穿出屋顶,几棵柿子树中间“长”出了一方咖啡露台。
本计划来这里游学一个月就走,仟一没想到正好赶上7月份在龙潭、四坪、墘头三村举行的“数字游民生活周”。她被游民和村民间随时随地的偶遇、共创吸引,后劲太大,就待到了现在,还找到了一份将第138号设计成数字游民基地的工作。基地是做什么的呢?仟一介绍:“游民们初到村里不知道住哪里、这个村是否适合自己的节奏,基地就扮演‘中介’,让游民们过渡一下。他们觉着村里哪个空间合适,就去哪里或长或短地工作生活。”她说的“空间”,在村里具象化为一处处可以做活动、工作、发呆甚至住宿的民居。
“随时大小班”“随处大小聊”,是这些空间给记者的感受。
晚上8点钟,天气有点冷了。在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溪龙乡横山村的DNA社区,透过落地窗可以看到静音办公室里还有不少人在工作。主理人梭梭在大屋顶下点起篝火,正聊着,陆续有人加入进来,有人烤肉串,有人玩火把,话题聊得很“飞”。大院子里的灯突然亮起,飞盘游戏开始。
DNA,是数字游民的英文Digital Nomad和安吉Anji的首字母组合。2021年之前,DNA是一间废弃的竹木加工厂,梭梭还在云南大理。“当时为何喜欢大理?风景、气候重要,但我和朋友们觉着更关键的是人跟人的关系。互相打招呼,互相很熟悉,这种归属感和交往给人滋养。所以我们就将这种大家共建共创且自由的社区复制到这里。”梭梭说。
白鱼是资深数字游民,创建了数字游民的线上社区SeeDAO。游民需要选择游到哪个具体的物理空间,一些活动也需要落地,在白鱼的考察和游动中,他最喜欢的地方是龙潭村。“好山好水的地方多的是,我觉得是这边的人让人喜欢。”白鱼说。
这种个人性、内在化的感受无法用语言准确衡量并表达出来,但听了很多故事后,总结起来,就是数字游民看重的不仅是换个低成本的地方办公,而是逃离城市钢筋混凝土带来的连对门邻居都不认识的疏离感。在乡村中,他们找到“活人感”,并期望共建一种不躺不卷且和其他人有边界互动的“新熟人社区”。
游到村里的年轻人的感受,让记者想到最近几年的热词:附近。这个词是人类学家项飙提出来的,指的是作为日常互动场所的邻里和工作空间。项飙认为“附近”的消失这一观点能引起反响,是因为它点出了年轻人的症结,就是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可以走,特别是从小地方出来的或者说一般家庭的孩子,只有考学这一条路。”对此,项飙倡导换一种视角看生活,看到周边的“最初500米”,还召唤艺术家、行动者们探索将附近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基础。
在屏南县,记者看到了一种正在广袤的乡村行动着的实践——乡村在变,青年也在变。
一年多前,本报推出的“艺术乡建”系列中就以《在这里,人人都是艺术家》为题进行过报道。此番采访,头顶是柿子树,背后是流水和各种空间叠加的乡村建筑,屏南县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总策划林正碌说:“工业文明给人带来的伤害是你站在高楼大厦下就感到渺小,而且作为普通人觉得人类太伟大的时候,想的是我什么时候能有个几平方米。但是坐在这里,像一只鸟飞到森林里,只要一停下来,整个森林都是我的,也不自觉地对柿子产生了一种审美和人文关怀。”
高楼和柿子,似乎代表了城市和农村两种生活以及看待生活的方式。听到林正碌的话,记者抬头正看见红红的柿子,想到了一句词:“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
中国近代著名社会企业家与乡村建设先驱卢作孚曾说:“许多青年,苦于没有出路;许多事业却又苦于没有训练成熟的青年去做。”这句话放在当前“人越来越少的乡村为谁振兴,缺乏人才的乡村靠谁振兴”这两大难处,且年轻人在乡村无用武之地的困境中同样合适。
坐在篝火边,梭梭说了多次“目的地”。“相比很多风景好、可以直接搞旅游的村,普通的村庄更多。从这个村切入,是想看看能做出一个可复制的模式,让普通的村也能吸引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毕竟,有了人,才有其他可能。”
采访时正赶上国仁乡建社会企业联盟和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组织的“乡村CEO与乡村运营”高级研修班来DNA参观,梭梭说这几年累计接待游民超过1.5万人次,来参观的人已没法计算了。“全世界有趣的人联合起来”几个字悬挂在社区的楼顶上,翻看DNA客服在朋友圈编辑的每日小报,会发现每天有不同人发起不同活动,采访当天一行人临时起意去爬山了,最近这些日子几个游民忙着在社区里开荒种地。就像点燃篝火后突然有几个人开始玩飞盘一样,游民们在园区里随时互动。
研修班有人问住房条件如何,梭梭说:“条件一般。”她笑着:“我们故意设计得一般,但设计了很多有意思且舒适的公共空间,这样他们就不愿在一般的房间躺着,而更愿到公共空间里来。一互动,活人感来了,创意也就来了。”
和DNA的“园区型”社区相比,屏南的村子里的游民则身处更大的社区之中,他们称之为“新型乡村社区”。
从10年前的艺术乡建开始,龙潭村、四坪村等村子陆续吸引了老村民返乡,也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在这里从事各种喜爱的事业而成为新村民,2022年,四坪村还在全国首创提出“云村民”。在龙潭村的警务室里,记者见到了辅警小倩,她是返乡青年,却常和新村民们打成一片。她既可说是老村民里的“新村民”,也是新村民里的“老村民”。过了一会儿,我们又相聚在了新村民思林的民宿边的银杏树下。她回忆:“数字游民周之前,讲真的,他们像来薅羊毛的。活动要来百十号人,组织者到处砍价。但活动开始后,村里每个空间都有活动,走进去一个就很热闹,有的活动持续到后半夜。”仟一在边上补充:“我就是那个经常玩到两三点的。就因为聊得好,所以被留下来负责设计第138号。”
两周时间,人文艺术类、科学技术类、社会组织创新类等120场不同类型的活动在村里的不同空间进行。思林端出柿饼来,说:“我家住的是区块链团队,天天在这讨论,我现在也算个专家了。”思林喜欢的不只是内容输出,而是久违的互动。他掰着手指算,2019年村里氛围很好,大家经常聊天。疫情后旅游突然火了,尤其是2023年7月进入旺季,忙了几个月后柿子又火了,又接着忙。“是挣钱,但我们来这里不是只为了挣钱,更看重在这里的生活,以及在互动中形成的韧性。除了商业可持续外,还有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亲密的链接。”他看着一起喝茶的另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小锤子,说:“我们是被吸引来做民宿、餐饮的新村民,有微妙的竞争。可因为经常互动,我们就不是熟悉的陌生人,很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游民的到来让思林他们怀念起了当年的热络,也反思新村民的创造性和热情消退后变为“旧”村民后的低沉,所以数字游民周结束后,他们又攒起了久违的朋友局,像白鱼一样很多游民也返场,留在了村里。10月份游民们和新老村民一起组织了象棋比赛,白鱼说:“象棋是村民们都可以参与的,活动不能只是游民们自嗨。”
“除了游民间、游民和村民们间的互动,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共建?”记者问。提此问题的原因,在于数字游民这个群体最先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出现,这个概念也早在上世纪末就诞生了。那些游民喜欢到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泰国清迈等地,原因就是“地理套利”,即用发达国家地区的高收入在物价较低的地区生活,实现货币价值的最大化。但这逐渐也产生新问题,就是数字游民虽带来一些短期消费,但会提高物价,甚至挤占当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并抢夺资源。
在国内,数字游民游到村时,一方面要看到他们地理套利的“利”,实际上是这些年各类的“乡建红利”,既包括水电路网气等基础建设,也包括像龙潭、四坪等村近十年来文创、农创、科创的积累以及乡村价值再发现后的各种激活,才使得游民能有“利”可套;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像白鱼、仟一一样的大量数字游民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参与到村庄建设中,并与新老村民共创共享乡村中的人文氛围与自然环境,而不是换个地方“996”或继续“黑白颠倒”。
白鱼认为,年轻人的优势就在于数字化,“要留下来,那一定是对这个地方有用,你有东西跟别人交换,别人才会需要你,你才能留下来。对年轻人来说,优势就是数字化。我感觉村里啥都自己可以搞定,但有一个东西搞不定,就是数字的东西。我听返乡青年说他回村里最大的贡献是教会村‘两委’用电脑。那接下来,我准备做的就是这个村的平台运营。比如社交媒体,再比如数字平台,村里每天来这么多人,这些流量怎么保存和利用?这些运营就是为了解决流量大但留量小的问题。”
严晓辉是香港岭南大学的研究员,也是国仁乡建社会企业联盟理事长,作为参与乡建二十多年的资深乡建人,他看到了像白鱼一样的数字游民在乡建中的价值以及乡村与数字人才的相互需要。今年7月,和全国乡村建设网络的二十个节点一起在屏南发起“乡建DAO”,既以“数字化”为引领推动乡建转型,也计划发起包括“程序员下乡”“产品经理下乡”等乡村数字人才计划。所谓DAO,是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即分布式自治组织的缩写。“乡建网络本来就是DAO,只不过缺少数字工具的使用。乡建DAO让愿意参与乡建的人有一个云端‘数字接口’,相当于乡建人的‘朋友圈’,无论谁,想为乡村做点什么,就可以进入乡建DAO线上社区,接着对应到很多个线下乡建‘节点’。大家游来游去,到村里有点事做,就变得有‘游’也有‘定’,能定,那就从‘游民’变‘有民’了。”
从游民到“有民”,或者说“数字游民2.0版”,就是因为这些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实践,正在突破和改写兴起于西方的与数字游民有关的概念甚至是行为方式——他们不仅可以几个人玩飞盘,也能和村里的人一起下象棋,从你、我到我们。
“坐好了,山路十八弯。”从宁德车站出来前往四坪村时,司机提醒。两个多小时的山路后,记者在黑夜中差点呕吐,开玩笑说:“这是山路一百八十弯,我明天得看看到底值不值得这场晕车。”司机笑答:“还是那片山,还是那些柿子,反正我们看习惯了。”
这场对话的内容,和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潘家恩的一次经历很相似。基于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的教学实践基地,潘家恩过去五年反复往返于闽渝两地,一次培训班上,他介绍完屏南这几个村后,一位重庆的村支书课间找他交流:“在你们‘城里人’看来‘是净土’,在我们‘村里人’看来‘净是土’。”潘家恩初到屏南时老拿着手机到处拍,尤其喜欢拍天,有村民嘀咕:“这有什么好拍的,天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些经历不由得让他思考这些“错位”背后的价值重估。“数字游民们喜欢的新熟人社会或者新型乡村社区,有着更为多元的联结方式,除老村民之间的血缘和地缘,还有村里新老业态互补互动所形成的‘业缘’,还有涉及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趣缘’。新主体和新技术带来新业态新关系,新业态新关系也让新主体有了留下来的新可能。”
华子来自东北,日常工作就是在网上通过公司接收订单,然后进行远程制图。工作自由,但让他痛苦的是玩伴们基本四散在全国各地,在家里没人玩儿。“我在网上看到了DNA,本来住一个月就走,现在决定待到年底。大家年纪差不多大,干啥的都有,还有很多‘大神’,大家随时就玩儿起来了,所以我在这里挺乐呵。有时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傻子,怎么这么乐呵。但我一想我还会画图呢,应该不傻。”华子睡到中午,外卖很快送到村里。吃完饭,空气清新,阳光正好,华子在院子里边遛弯边说。
对村庄的价值重估的基础,是农村短板逐渐补上之后,长板价值的凸显。正如林正碌十年前就说到的“地理大发现”:“新时代的山区里古代‘愚公’渐渐消失,因其所关心的交通、劳动及生活便利等问题,正被工业文明与当前各级政府逐步解决,眼前不仅无需移山,还倡导守护‘青山’。这时候看山的人变‘李白’了——‘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采访时,四坪村的上空盘旋着很多无人机,人们在村里拿着手机走走停停。潘家恩说到自己关于“净是土”和“是净土”的“错位”思考时说:“这些山村里的新现象,反映了城乡融合与生态文明转型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新时代下包括主体、业态、空间、技术、关系、生活方式在内的新变化,人们自然要突破对乡村的固有观念与定型化认知,从价值层面上对转型时代乡村的新坐标和新可能进行探讨。村庄‘老树发新芽’的可能性如此之大,像数字游民一样的不同群体也有‘不卷不躺、亦城亦乡、半码半农’的别样选择。”
说着,红色的柿子和远处青山映衬着,潘家恩又不自觉地拿出手机拍了几张。曾经,山没什么价值,山就是山;后来,山上有各种可开发的原材料,那么山不是山;如今,与山相看不厌,山与“我”同在,山又成了山……(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巩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