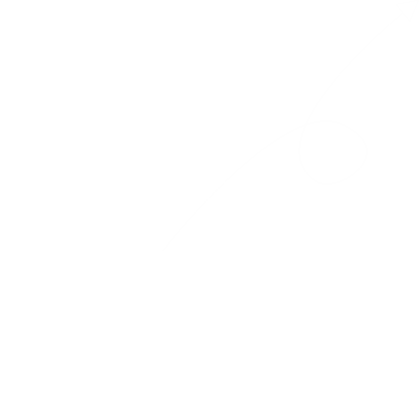离乡四十载,最是那春节里的乡戏,像一根看不见的线,轻轻一扯,便牵着游子的心朝着故乡的方向跌去。一座简朴的戏台,几盏明晃晃的汽灯,便是全部了。可那婉转的唱腔一旦扬起,斑斓的衣袂一旦舞动,十里八乡的人们,便像被磁石吸着,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台下时而响起的叫好,混着瓜子壳落地的细碎声响,便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网,网住了一整个春节的人情与年味。
在我的江南故乡,春节与唱戏,是分不开的。田垄尚在冬眠,人心却早已被锣鼓唤醒。逛庙会,看大戏,记忆中是年该有的样子。大戏开场的锣鼓声总带着一股莽撞的喜气,锵锵地撞进人们的耳膜。接着,生旦净丑次第登场,水袖翻飞,唱念做打。台下的人,仰着脸,眼神亮晶晶的,随着剧情忽悲忽喜。那份专注的欢喜,是平日里难以见到的风景。
父亲今年八十多了,是个十足的老戏痴。自我记事起,他便是戏台前最忠实的观众。母亲总笑着说,他年轻时,为了追一出好戏,能走上十几里夜路。许是幼时总被他牵着手,挤在弥漫着烟草与尘土气味的人群里,那咿咿呀呀的调子,早已和父亲的体温一道,渗进了我的血脉。如今回家过年,第一句问的常是:“爸,今年戏台搭在哪儿,几时开锣?”
去年腊月归家,父亲眉眼带笑:“初一就开戏,在祠堂前头,连唱三天!”语气里满是孩童般的期盼。腊月里阴雨缠绵,到了初一,竟奇迹般地放了晴,天蓝得像一匹刚浆洗过的绸缎。乡里的规矩,戏要从午后一直唱到群星满天。为了占个好位置,我和妻早早扛了长凳去。原以为算早了,到了才发觉,戏场早已是人山人海。台前黑压压一片,怕是有好几百人。场子外围,临时支起的小摊热气腾腾,甘蔗的甜、糖葫芦的亮、炒瓜子的香,混杂着孩子们的追逐笑闹与零星的鞭炮声,空气里酿着一团浓得化不开的、属于世俗的快乐。
下午一点,锣鼓准时敲响。头一出是庐剧《秦香莲》,这是我从小看到大的。那熟悉的悲情调子一起,台下许多花白的头便跟着轻轻点动。唱到《公堂》一折,包公那一声怒喝,台下顿时爆起一片“好”来,掌声雷动,那是观众与戏文最直白、最酣畅的交流。第二出却是新编的现代小戏,叫《七品河长不一般》,讲的是治污护水的新故事。台上演的虽是今人事,那份为民请命的心肠,倒与古时的清官戏一脉相通。
父亲在一旁慢悠悠道:“八里外黄村,唱的是黄梅戏。”妻儿一听,便转场而去。到了黄村,景象果然不同:黄梅戏婉转清甜,观众里多了许多明艳的衣衫,年轻的面孔,尤其是姑娘们,三五成群,笑语盈盈。台上正唱着《夫妻观灯》,那份活泼泼的喜悦,仿佛要溢到台下来。妻子也跟着轻轻哼唱,举起手机,将这份热闹定格,分享给远方的友人。
整个正月,村村都有戏。那些日子里,家家户户的亲戚都格外多。远道而来的,一半是为拜年,另一半便是为着这共同的戏。我家也一样,姑姑、姨娘、舅舅,都从十几里外被父母邀了来。彼此间或许没有太多热烈的言辞,只是并排坐着,在同一阵锣鼓里点头,为同一句唱腔叹息或喝彩。
“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如今想来,那正月里的乡戏,哪里仅是戏呢?它是一种传承,让古老的忠孝节义、今天的山河新事,在一代代人的注目中活下去;它更是一座温情的桥,连着故土与游子,系着旧岁与新春。当最后一个音符在清冷的夜气中散去,人们拍拍身上的尘土,满足地归家时,带走的,是一整年的踏实,和对新一年无声的期盼。
那戏台上下交织的声与光、情与暖,才是年最深、最迷人的味道。(汪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