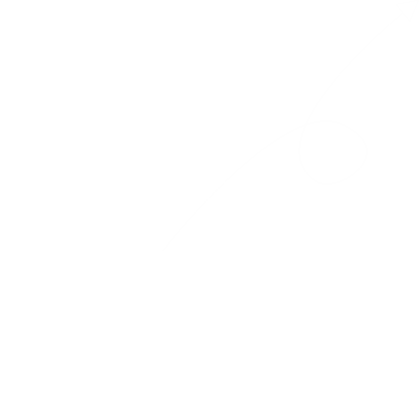王永利/文 一个是急速扩张,一个是逐渐缩减。
前者是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其从今年2月末的4.26万亿美元,急速扩张到4月15日的6.37万亿美元,增长了将近50%;
后者是中国央行的资产规模,从2019年末的37.11万亿元,缩减到2020年3月末的36.54万亿元,降幅1.5%。
二者之间隔着不同的调控环境、工具与任务。这也是缘何资产规模与货币总量的变化并不成正比。资产规模大不意味货币总量就大,反之亦然。
或许,不能仅从央行资产规模的变化上简单类比,认为美联储“疯狂大放水”,将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反观中国央行,其货币政策是否过于“稳健”?能否在面临疫情严重冲击时及时发力,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疫情来临,中美央行资产规模变化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为什么面对重大冲击,宏观调控越来越依赖货币政策?费雪货币数量论强调“MV=PQ”(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水平×可交易财富数量),宏观形势剧变的今天,这个经典理论,或者说货币相关公式可否改为ML=PQ(L为流动性)呢。
追本溯源中国央行、美联储的资产规模与货币总量之变,从五个方面去看中美两国央行的货币调控环境与任务,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货币政策应对危机的答案。
两大央行的资产规模与货币总量之变
新冠肺炎疫情大规模爆发,对中美两国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亟需采取强力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予以应对。
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自3月3日开始,不仅快速将联邦基金利率(基准利率)从此前的1.5%-1.75%降低至3月15日的0%-0.25%的基本零利率水平,而且从15日开始推出大规模量化宽松(QE)政策,其资产规模急速扩张(扩表),从2月末的4.26万亿美元,急速扩张到4月15日的6.37万亿美元,增长了将近50%,而且根据美联储3月23日已经发布的“无限量QE”声明和相关计划,近期其资产规模仍将大幅度扩张,有人预计到年末可能超过10万亿美元。
但是,与美联储不同的是,面对疫情冲击,今年1季度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规模却不升反降,从2019年末的37.11万亿元,缩减到2020年3月末的36.54万亿元,与美联储资产规模的变化出现了巨大反差。
但这种状况的出现,实际上是与中美两国央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调控对象、可选工具、传导效率等因素密切相关的,需要深入分析,不能仅从央行资产规模的变化上简单类比,就认为美联储“疯狂大放水”,货币政策极度宽松,将引发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过于“稳健”,不能在面临疫情严重冲击时及时发力,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
这至少需要从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规模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A. 中国央行资产规模及相关因素与货币总量变化情况
从中国央行公布的资产负债表中可以看出,其资产负债规模的变化,主要受到央行外汇占款(资产)、存款性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央行负债,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及超额准备金存款)、央行对存款性机构拆放资金(资产)三大因素影响,其相互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
其中,2000年以来,央行外汇占款不断增加,直到2014年5月达到高峰。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外汇占款出现持续缩减态势,特别是2015和2016两年大幅缩减。央行外汇占款属于基础货币投放,其扩大会相应增加商业银行存款,并支持商业银行扩大贷款,如果不加以调控,货币总量会随之出现更大规模的扩张。同样,其缩减会相应减少商业银行存款,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投放,如果不加以调控,货币总量就会随之出现更大规模收缩。
在央行外汇占款不断扩大情况下,为控制货币总量过快过大增长,造成货币严重超发,央行随之不断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准率),相应冻结商业银行越来越大规模的资金,抑制其贷款投放及其派生货币(存款)的扩张。存准率在2003年9月,将之前保持将近4年的6%提高到7%,之后不断提高,到2008年6月,提高到17.5%。在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后,央行迅速下调存准率至16.5%。向商业银行释放流动性,支持其扩大贷款投放。
2008年12月,进一步将大型银行存准率下调到15.5%,中小银行存准率下调到13.5%。但随着央行外汇占款快速扩大,央行于2010年1月转而开始提高存准率,将大型银行存准率提高至16.0%。之后不断提高,到2011年6月,将大型银行存准率提高至21.5%,中小银行存准率提高至18.0%。这样,就在外汇占款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整体上保持了货币总量的平稳增长,并没有因央行外汇储备的大规模增长而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为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央行从2011年12月开始下调存准率,大型银行下调至21.0%,中小银行17.5%。到2016年3月,大型银行下调至16.5%,中小银行下调至13.0%。之后,为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避免“大水漫灌”式货币投放,央行不再实施普遍降准,转而改为小幅度的定向降准,直到2018年4月,再次启动普遍降准,将大型银行存准率下调至15.5%,中小银行下调至12.0%。之后,采取普遍降准与定向降准相结合的方式,;到2019年12月将大型银行存准率降至13.0%,中小银行降至11.0%。2020年进一步加大降准力度,到3月份平均存准率已降低至9%,且4、5月份仍会下降。这样,就在外汇占款下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继续保持货币总量总体上的平稳增长,体现出稳健货币政策的基本要求。
央行外汇占款扩大,相应提高银行存准率,就会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规模。相反,央行外汇占款减少、相应降低银行存准率,就会缩减央行资产负债规模。银行在央行的存款规模受存准率提高或降低的影响很大。
在央行外汇占款收缩,但降低存准率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满足央行扩大贷款投放需要的情况下,央行为缓解商业银行流动性紧张局面,相应就要扩大对银行的资金拆放。所以,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央行拆放商业银行的资金规模(对存款性机构债权)快速扩大。这又会在央行外汇占款和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减少情况下,成为央行资产规模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
正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尽管中国央行的资产规模到2019年末比2008年8月末扩大了不到2倍,但同期中国的货币总量却扩大了将近4.43倍。其中,2009年末货币总量比上年末更是大幅增长了28.4%。2020年1季度末,央行资产规模比上年末减少了1.56%,但货币总量却增长了4.75%。
B. 美联储资产规模与美国货币总量的变化情况
从美联储资产规模与美国货币总量的变化情况表可以看出,2008年8月以来,美联储资产规模的阶段性波动是非常大的,其中出现三个明显阶段:
一个阶段是2008年9月雷曼公司倒闭后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美联储为救市而大规模投放流动性,其资产规模随之大幅度扩张,到2008年末即达到2008年8月末的2.46倍以上(不少人惊呼“美联储开足马力印钞票”)。
再一个阶段是2013年开始实施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大量向金融机构购买资产投放流动性,到2013年末美联储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美元。
还有一个阶段是2020年3月开始,启动新一轮QE,甚至是无限量QE,美联储资产规模出现陡然扩张的态势,到2020年4月15日,已相当于2008年8月末的近8倍。
但与美联储资产规模大幅度扩张不同的是,美国货币总量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当年末货币总量仅比8月末增长6.36%,2009年末比2008年末也仅增长3.78%,远远低于当年中国M2增长28.4%的速度。2020年3月末M2余额仅相当于2008年8月末的2.09倍,远低于中国同期的接近4.64倍。
不同的货币调控环境、工具与任务
迥然不同的资产规模与货币总量背后是中美两国央行货币调控的环境、工具和调控任务存在巨大差异。
对比中美两国央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货币政策的调控环境、调控对象、可选工具、传导效率等因素,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存在五大差异:
a、由于美元属于国际中心货币,美联储实际上成为世界隐形中央银行,所以,美联储几乎不需要外汇储备,也就几乎没有外汇占款。同时,早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前,美联储就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黄金储备(当时约占全世界官方黄金储备的80%以上),这也成为美元坚持与黄金挂钩并取代英镑成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重要原因。到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彻底废除金本位制之后,美联储依然持有超过8000吨的黄金储备并继续雄踞世界第一(成为美元价值的重要支撑),几乎无需扩大黄金储备,增加黄金占款。这就使美联储不会像中国央行一样,通过扩大黄金或外汇占款扩大基础货币投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央行的外汇占款不断增加,到2014年5月高峰时达到27.30万亿元,之后开始下降,但至今仍保持在21万亿元以上,成为央行资产中最大的构成部分,成为与美联储资产结构不同最重要的因素。
b、二战之后,美国建立起高福利社会制度,失业和低收入救济、医疗和养老保障、子女教育等,基本上有政府基金提供支持,居民个人基本上无需为此保留储蓄,相应就造成储蓄率很低,而负债率和金融投资率较高,社会投资又更多地以机构投资者为主。这就推动美国直接融资高度发达,但间接融资占比较低。中央银行无需像中国央行一样,更多地关注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的增长和货币总量的变化,而主要是关注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变化以及利率水平的变化。在基准利率降低至零利率,直接的资金拆放难以扩张时,就只能采用量化宽松的方式调节流动性。
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中国的社会储蓄率远高于美国,中国直接融资不够发达,间接融资占比非常高,所以货币政策上更多的还是关注信贷投放和货币总量的变化,而不是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变化。目前,中国还没到基准利率为零的程度,降息和扩大资金拆放依然存在很大空间可以利用,还没到需要启用量化宽松的时候。
c、美国强调自由市场制度,在金融市场上更是如此,主要采取市场化手段进行调控,而反对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由此,美国很早就开始推行商业化存款保险制度,相应的减少乃至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使用。这就使美联储无法像中国央行一样,通过存准率的提高或降低调整流动性。
中国近期尽管存准率有了较大下降,但整体上依然保持在9%左右的水平,即使与2003年9月前的6%相比,依然有3个百分点左右降准空间。如果跟美国相比,则降准空间更大。而通过降准释放流动性,会减少而不是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规模。
d、由于,美元是国际中心货币,美国金融市场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不仅仅是美国人的金融市场),其金融市场流动性实际上是全世界美元流动性的集中表现场所。随着全球货币总量和负债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金融市场流动性波动的规模和幅度也越来越大,这就使得美联储在保证市场流动性供给和调节上,任务越来越艰巨,需要调整的规模越来越大。
相对而言,中国金融市场目前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基本上就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金融市场,因此,中国央行调控市场流动性的压力远比美联储低的多。
e、美联储主要注重于解决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并通过利率和流动性调整引导金融机构扩大货币投放,引导社会主体扩大投资和消费,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相对较低,特别是在面对严重的通货紧缩(社会主体不愿扩大负债并用于投资和消费)压力下更是如此!
相比而言,中国在面临经济下行、通货紧缩时,国家不仅可以运用市场化经济手段进行引导,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运用行政手段、组织措施推动政府和国有企业扩大负债和投资,推动国有金融机构扩大货币投放等,所以,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相对更高。
货币公式可否改为:ML=PQ
如此,正是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中美两国央行资产规模的扩张与货币总量的增长存在巨大反差,需要准确认知和把握,不能简单地按照中国的情况去看待美联储的资产规模大幅度扩张,并认为其无限量QE必然导致其大放水,大放水必然造成货币严重超发(“开足马力印钞票”),进而必然导致严重通胀和货币贬值,乃至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实际上,美联储大量投放流动性,恰恰是在面对危机威胁时,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必要手段,并不必然引发货币总量更大规模的扩张,而且在危机解除,通货紧缩转向通货膨胀时,又可以及时采取反向政策收缩流动性,压缩央行资产规模。同样,也不能因为中国央行资产规模没有像美联储那样的规模扩张,就认为中国的货币总量就不能快速扩张,中国货币政策不能充分发挥积极刺激作用。
关于这一点,笔者早在2012年就通过对比分析金融危机爆发后,美、中、欧(欧元区)、日、英等主要国家央行资产规模与货币总量变化的关系指出:货币总量的变化受到基础货币投放和货币乘数(流动性)变化的共同影响,不能简单地认为央行资产规模扩张,就必然导致货币总量更大规模的增长,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后,(到2011年)几大主要国家中,中国央行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最低,但货币总量扩张的速度却是最高的;美国央行资产规模扩张是最大的,但美国货币总量的增长适度远低于中国。
进一步看,为什么面对重大冲击,宏观调控越来越依赖货币政策?为什么日本、美国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央行可以大规模扩表,向市场释放巨额流动性,但其货币总量却并没有同步增长,没有出现恶性通胀,反而出现日益增强的通货紧缩?这需要重新反思“货币总量、货币流动性与财富规模、物价指数”的关系。
经典的“费雪货币数量论”强调“MV=PQ”,但却认为货币流通速度V由社会制度和传统习惯等因素决定,基本保持稳定,也可视为常数;可交易财富数量Q,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产出水平相对稳定,也可视为常数,这样,价格水平P的变动仅源于货币数量M的变化,二者会保持同比例变化。货币数量增加必然引起物价水平上涨,或者说物价水平的普遍上涨只能是货币数量扩张引发的。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除坚持上述结论外,又进一步得出结论:当出现通货紧缩时,也必须扩大货币数量。于是,“温和通胀”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就成为货币主义的政策目标。
但费雪货币数量论与弗里德曼货币主义都存在很多假设,其中,最大的假设是:人们持有货币的目的就是用于交易,货币会充分流动。实际上,货币总量中会有很多被闲置或藏匿而停止流动,并不是充分流动的。这样,货币总量就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流动性(L)问题,即货币总量中真正处于流动中的货币数量占货币总量的比重(L不同于V)。
由于流动性的客观存在,而且其变化不仅受到央行和金融机构的影响,更受到企业、家庭和政府等投资、消费偏好的影响,变化幅度和影响程度会很大,所以,真正对物价水平构成影响的,主要不是货币总量,而是其中流动中货币数量,即ML:即使货币总量的增长超过财富数量的增长,但流动中货币数量的增长低于财富数量的增长,其结果并不是物价上涨、通货膨胀,而是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因此,货币相关公式可否改为:ML=PQ。在货币政策上,不应该过度关注货币总量的变化,而应该高度关注流动性的变化(参见《经济观察报》发布的笔者文章《宏观调控为什么越来越依赖货币政策》)。
基于上述分析,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大爆发,其对全球经济金融和社会运行的影响仍在加深(其中,4月20日美国WTI原油期货市场交易合约居然出现史无前例的负价格,当天收盘于每桶-37.63美元,盘中一度达到每桶-40.32美元,给国际金融市场造成新的很大冲击),国际经济往来严重受阻以及两国关系趋于紧张,可能会影响和冲击我们的经济增长。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巩固和增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与国际地位,困难和挑战极大,中国亟需尽快推出一揽子超常规强力宏观调控政策,其中,货币政策更应该发挥重要的先导引领和支持作用。
(作者系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