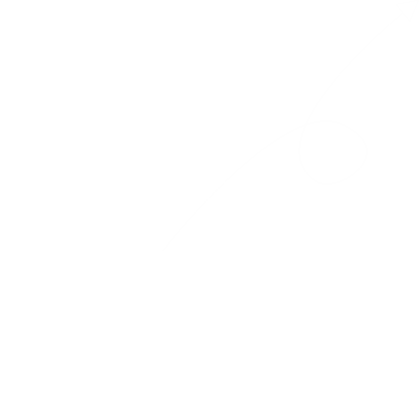国际管道中乌项目布哈拉输气处生产技术科科长 陈子鑫
8年前的这会儿,我正纠结:得到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保送研究生的名额,同时,拿到了中亚天然气管道公司的录用通知。
我跟外公和我爸说:“我要回到中石油。”他们异口同声——反对。
其实,对于他们的反对,我并不惊讶。
外公今年81了。对于他的过去,我只知道个大概:16岁入伍,20岁转业,成为玉门油田的石油工人。1960年参加大庆会战;7年后,参加四川石油会战;然后又回到大庆,成了八三管道建设的一员。
按说以他的年龄和经历,应该有很多故事。但是很遗憾,外公很少跟我讲。
去年,我看了《大庆魂》记录片后很感动,休假回去问他,被他顶了回来:过去那些事提他干啥?倒是外婆的回忆,弥补了这段空白。
在大庆,外公住的是存放工具的库房;刚去大庆那会外婆关系没转过去,外公一个人挣钱要养活五张嘴。当时家里仅有的白面给了刚出生不久的舅舅,剩下的都是吃苞米茬茬。有段时间外公饿的掉头发,别人以为他得了麻风病,都躲着他。
我理解,外公反对我加入石油队伍,是因为留在他记忆里的那段岁月,是艰苦的。
我的父亲一名管道无损检测工程师,常年随项目在野外工作。因为我和他没有太多共同经历,我也不想他,我不知道该想他什么。倒是我爸每次回来,都会让我靠着墙,用尺子比划着在墙上画一条线,旁边标着高度和日期。这一条条间隔不等的身高线,就是我爸回家的日子。其中间隔最长的,是15厘米,而时间,整整是一年半,那时我爸在苏丹工作。
1999年1月,春节将近。我爸从苏丹来信说过年回不来了。公司就组织我和妈妈这样的家属拍录像,带到苏丹,年三十儿晚上再播一下,就当拜年了。我爸就这么贴着电视,和录像里的我和我妈,拍了一张别样的全家福。
现在我理解,父亲反对我加入石油队伍,是因为留在他记忆里的那段岁月,除了艰苦,还有与亲人的离别。他不希望我再重复他们的生活。
但我选择中石油,是因为回到中石油让我有归属感。
我是在石油大院长大的,虽然我爸不在身边,但周围有着一群像我一样的小伙伴,并不孤单,每年的合唱比赛都要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大院里邻里之间也相互照顾,我妈下班晚了,我就在邻居家玩,有时顺带把饭也蹭了。初三时,我生病,妈妈弄不动我这个大块头,情急之下一个电话打到爸爸单位,马上就有人把我抬到医院。这份集体的感情至今依然温暖着我,石油的种子就这样埋在了我的心底。
对于未来的选择,我也思考了很久,最终,我决定顺从自己的内心,放弃保研,选择石油。当我把我的决定告诉父亲时,我在他的反对声中,感觉到了他眼神中闪过的一丝欣慰。
就这样,我来到了中亚,在荒芜的大地上扎下了根。工作的压缩机站,地处乌兹别克斯坦无人区,离最近的城市开车要两个多小时。
八年来,我体验到了外公不愿讲起的艰苦,我经历了父亲经历的孤独与寂寞。
渐渐我知道了,为什么抱着电视机照的那张全家福,在父亲的心中那么珍贵,因为每一次的团聚都来之不易;渐渐我知道了,为什么每次回家我爸都会带那么多的土特产,因为“买买买”可以寄托思念;渐渐我知道了,为什么每次回家他总是大口大口吃蔬菜,因为上了“线儿”,新鲜蔬菜是“稀罕物”。
就是在这些“渐渐”中,我读懂了父亲,读懂了“石油人”。也让我思考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为什么我们建设大庆要受这些苦,为什么我爸去苏丹工作一年半回不来?说到底还是我们落后,还是我们底子薄,没有世界先进大公司的积累。我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有了他们的累积,是不是应该做的更多。
首先就是学技术,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工程师。作为一名生产人员,只有技术立身,说话才能有底气,才能让合作伙伴信服。刚投产那会,我们既是调度,也是工程师,还是翻译,白天没时间学习,就利用值夜班的时间学。而且还要带着问题去学,提前把图纸、资料看完了,趁着调试的间隙想尽办法问问题。平时多打个下手,麻利点,和各位老师傅搞好关系,也好多学几招。
自己学会了之后还要教,因为我会休假,设备不会休假,要培养我们所在国的当地员工,教会了他们,管道安全运行也更有保障。常常可以看到我这样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员工在带领和指导四五十岁的当地员工开展工作。而我们培养的当地年轻技术骨干,也成为所在国其他公司争抢的对象。
有个当地员工叫老卡,是我的忘年交,我就是他嘴里的“别人家的孩子”。老卡总说我是他的小儿子,如果他还有未出嫁的女儿,一定要把女儿嫁给我。
技术上的钻研和成长,让我们赢得了乌方同事的信任和尊重,更收获了理解和友谊。
休假的时候,我跟外公说,您那个时候是人拉肩扛建设大庆,我爸那会儿是翻山越岭在各地建管道,而我现在是在“一带一路”上继续着你们的事业。外公欣慰地笑了。
这就是我们一家三代石油人的故事。外公和父亲,把艰苦奋斗、仁忍担当的家风传给了我。我想我们中国石油也有一种家风,那就是以苦干实干、三老四严为核心的石油精神。也正是因为这种“家风”的传承,中国石油才能攻坚克难、发展壮大。我和我的同时代人,将继续把这种“家风”传承下去,让石油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