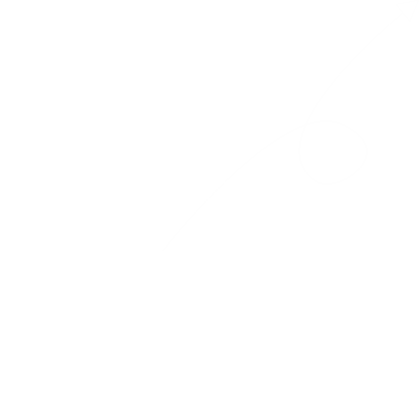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随着互联网贸易的兴起,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也逐步拓展到新型贸易领域。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WTO协定至今未能制定出反映时代变化的互联网贸易新规则。由此,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行场所转向的策略,试图从区域或双边经贸规则出发,构建互联网贸易的规则体系。
·新一代经贸协定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互联网贸易新规则。第一类为限权性规则,要求缔约方不施加不必要的电子贸易障碍措施。第二类为赋权性规则,要求赋予贸易商信息自由的权利。
·当前,我国网民数量已牢牢占据全球第一,我国已成为互联网贸易大国。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伟大目标。在新时代,构建体现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利用好、发展好、维护好互联网贸易规则。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通信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第五空间。人类通过互联网技术创造出一个与实体空间相平行的网络社会,并促进跨境贸易更加自由化和便利化。当前,绝大多数经济和社会活动都能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互联网贸易也成为当前众多贸易活动的主要形式。与实体贸易相同,互联网贸易亟须通过法治化的规则进行治理。
互联网贸易将成为未来贸易活动的主要形式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技术变革之一,互联网技术成为驱动经济全球化的显著力量。欧盟委员会报告曾指出,未来的绝大多数经济活动将会高度依赖电子系统、网络基础设施、软件和应用程序、网络数据等。无疑,互联网贸易将成为当前和未来的外贸新增长点,其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互联网技术促使传统的实物商品电子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更多的商品将以电子方式表现。例如,传统的唱片、书籍等实体货物贸易大多可转化为服务贸易。产品服务化使得商品在生产者、销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传输成本更小、时间更少、效率更高,进而推动贸易的增长。
第二,网络平台成为商品交易的便利渠道。网络平台包括搜索引擎、社交网站、电子商务平台、应用商店、评级网站等,它们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愈发凸显。例如,现代银行和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开放的通信通道,并向客户提供离柜金融服务。网络平台使得消费者能够及时发现互联网贸易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信息不对称、双方议价能力失衡等痼疾,进而创造更大的交易量,并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福利。
第三,互联网技术催生新动能和新行业。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方位发展,云计算、物联网、3D打印、人工智能等新型服务行业应运而生。例如,通过深度学习,智能机器人已成为运算、速记、翻译、法律等服务提供者。互联网技术源源不断地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推动形成现代化的外贸经济体系。
限权性规则和赋权性规则:互联网贸易新规则的主要形态
随着互联网贸易的兴起,传统的国际贸易规则也逐步拓展到新型贸易领域。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多边贸易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服务贸易总协定》《电信附件》《电子传输免税备忘录》等文件实现互联网贸易的自由化。
具体而言,《服务贸易总协定》是规定具体服务类型的文件。在该协定中,WTO成员在其服务承诺表明确试听服务、计算机服务等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义务。与计算机相关的服务类型分别为计算机硬件安装相关的咨询服务、软件启动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库服务、其他服务。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只有成员做出肯定性承诺,其才承担相应的服务贸易自由化义务。《电信附件》则是针对互联网通信功能的文件。其规定成员应确保互联网的互联互通,并保障互联网成为有效的产品分销媒介。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文件均缔结于20世纪90年代,前互联网时代的多边贸易规则无法预见当下的互联网经济生态。例如,当时的谈判缔约方将互联网服务分为以传输为目的的电信服务与以内容为目的的试听服务。然而,新型的互联网服务类型兼具传输性与内容目的性双重属性,例如,即时媒体视频服务、网络电话等。同时,由于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WTO协定至今未能制定出反映时代变化的互联网贸易新规则。由此,以美国、欧盟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行场所转向的策略,试图从区域或双边经贸规则出发,构建互联网贸易的规则体系。
《美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简称美韩FTA)是首个规定信息自由流动的FTA。该协定第15.8条规定:“认识到信息自由流动对促进贸易的重要性,以及承认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缔约双方应努力避免对跨境电子信息流动施加或维持不必要的障碍。”随后,《加拿大—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协定)、《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和贸易协定》等新一代经贸协定也有相似规定。
具体而言,新一代经贸协定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互联网贸易新规则。
第一类为限权性规则,要求缔约方不施加不必要的电子贸易障碍措施。限权性规则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缔约方不应以不适当的电子方式阻碍贸易;二是,与其他方式相比,缔约方不应对电子方式提供的贸易施加更具限制性的措施。例如,TPP协定第14.11条指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措施应满足两个条件:(a)不得以构成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方式适用,或对贸易构成变相限制;(b)不对信息传输施加超出实现目标所必要的限制。”
第二类为赋权性规则,要求赋予贸易商信息自由的权利。以TPP协定电子商务章节为例,其要求成员确保全球信息和数据的自由流动,承诺不施加对当地数据处理中心的限制,并承诺不要求转让或评估软件源代码。同时,该协定还直接规定缔约方不应对电子传输征收税收,不通过歧视性措施或彻底屏蔽的手段支持国内生产者或服务者。本质上,赋予贸易商信息自由要求排除对信息自由和商业自由的非法干扰。当然,贸易商信息自由应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隐私等价值相平衡。TPP协定第14.11条也规定电子跨境传输的自由化不得阻止缔约方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而采取或维持的限制性措施。
值得说明的是,除上述两类规则外,互联网贸易规则还涉及到知识产权保护、中小企业能力建设、贸易便利化、金融服务等具体领域。
互联网贸易规则遭遇碎片化的挑战
由于互联网技术瞬息万变,互联网贸易方式、形式和模式也是开放的、持续变动的,由此,与传统的贸易规则相比,互联网贸易规则的制定与适用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互联网贸易规则的法律效力呈现软法化。传统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为国际条约和习惯国际法。然而,由于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并且网络大国对互联网贸易规则的认识存有分歧,软法治理逐渐在互联网贸易中占据主导作用。一方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不断发布关于鼓励数字经济发展的示范性文件,引领形成互联网贸易领域的国家共识;另一方面,区域或双边经贸协定中的互联网贸易规则多体现激励性的特征。例如,美韩FTA仅规定缔约双方“努力”避免实施或维持不必要的电子贸易障碍。在法律上,该“努力”术语难以具备法律拘束力。
第二,互联网贸易规则的权利属性呈现多面性。由于网络空间为人类生活的新空间,其涉及多种权利属性,这也导致难以对互联网贸易规则进行定性。例如,美国主张互联网接入权受国际贸易协定的约束,其为贸易议题;而法国等欧盟国家认为互联网议题为人权问题,其反映个人的发展权。当前,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协定承认互联网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提升贸易机会的重要性。例如,TPP第24章“中小企业”规定,各成员应通过提供网络信息和链接的方式,增加中小企业的贸易机会。
第三,互联网贸易规则的谈判场合呈现多元化。传统上,WTO和区域经贸协定是实现各国经贸规则统一化的主要场所。由于互联网贸易议题的重要性与广泛性,其也频繁出现在国际电信联盟、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互联网管制论坛、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二十国集团等场合中。例如,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通过并发布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鼓励促进经济增长、信任和安全的信息流动,利用互联网促进产品、服务的创新,并实现电子商务跨境贸易便利化。
中国应成为互联网治理法治化的推动者
2017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提出,亚太地区应深化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合作,引领全球创新发展的方向。
21世纪是互联网的时代,中国长期以来致力于推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全面发展。当前,我国网民数量已牢牢占据全球第一,我国已成为互联网贸易大国。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中国”的伟大目标。在新时代,构建体现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利用好、发展好、维护好互联网贸易规则。
在对外缔约层面,我国应积极打造符合中国及世界经济利益的规则文本。提升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是我国实施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互联网贸易规则呈现碎片化的背景下,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主动从互联网产业需求与各国博弈焦点出发,在明确中国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具备国际吸引力的提案与草案。2016年11月,中国政府首次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电子商务倡议,然而,该草案并未直接涉及数据流动、网络技术标准互认等信息时代的核心议题。在未来的倡议和谈判中,我国政府应争取在核心议题上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
在国内立法层面,我国应主动创设具备示范效应及推广价值的法律文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率先开展网络空间法治化治理进程,并相继公布《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民法总则》等法律文件。由此,保障网络安全的“四梁八柱”总体框架已基本稳定。下一步,我国应在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前提下,探索建立推进互联网贸易、加强网络信息利用的法律规定,进一步释放数字红利。例如,2017年10 月,我国公布《电子商务法》(二审稿),该草案分别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规制,并强化商务平台的交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责任等。作为网络大国,我国应不断归纳本国创新性立法及其司法经验,通过国内法治对国际法治的示范与引领作用,使互联网治理的先进成果惠及全球。
在执法层面上,我国应坚持在非歧视基础上对互联网贸易活动进行合法规制。WTO协定与新一代经贸协定的宗旨在于确保贸易政策不构成不必要的贸易障碍,以实现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由此,除实现保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合法目的外,我国应避免实施或维持限制互联网贸易的措施。2017年9月,美国在WTO指控中国《网络安全法》的实施将对跨境贸易活动产生限制。我国应积极运用WTO规则进行抗辩。在具体执法中,我国应坚守非歧视性要求,明确认定互联网贸易规则仅适用于贸易领域,有理有据地通过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规则佐证互联网贸易限制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在守法层面上,企业在互联网贸易领域应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商事主体应积极利用互联网贸易规则抵制歧视性的政策和措施,并限制国家权力的非法干预,提升通过电子手段获得贸易机会的能力。同时,中小企业也可主动与WTO等多边经济组织联络,加强自身电子商务能力的建设。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企业应尊重各国的网络主权。由于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互联网普及程度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关切不同,因此,各国尚未实现互联网规则的统一化。因此,企业应尊重各国制定网络空间行为规范的权力,遵守进出口国的互联网法律规则,以此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