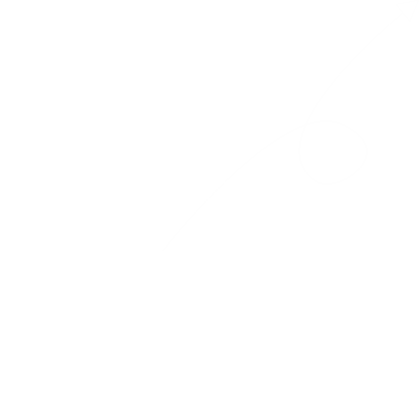又一年清明节快到了,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这个特别的传统节日里慎终追远、怀念故人。究竟什么是生命的意义?我们应该有怎样的生死观?从福寿园国际集团首席品牌官伊华和临终关怀志愿者纪慈恩的演讲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迪。
向死而生,你才能了解生命真谛
伊华
这个行业也是需要美的
我是来自殡葬行业的一名女性从业人员,从1996年进入这个行业,至今已有24年。我为什么会进入这个特殊行业工作呢?
16岁那年,我曾是中国第一代的时装模特。那时的我,像每个女孩一样,有着美好的憧憬,希望呈现最美的自己。但我出身于教育世家,爸爸妈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一致反对我当模特,所以我的模特梦没有实现。
后来,我又进入外资企业工作,还曾经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过市场营销总监。那时我才二十几岁,但是,我觉得富足和安逸来得太早,对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意义,反而会成为前行道路上的阻碍。因此,1996年6月1日,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没人敢去甚至很多人忌讳的殡葬行业作为我未来的事业。
这个决定,当然再一次在家庭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我的爸爸妈妈说:以后人家问我们,“你女儿在哪里工作?”我们说不出口,也抬不起头啊。其实,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我深深体会到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于是,我对我妈说:妈,你给我一点时间,我希望能够带领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登上大雅之堂,因为这是所有中国人都需要的服务,它也是需要美的。
今天,我可以很自豪地说,在这24年的从业过程中,我只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把殡葬做美。
我希望这种美能够透射出家庭的情感、社会的温度,能够让更多的人在告别亲人的这一刻感受到生命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是把公墓变成公园,第二件是让告别变得美丽,第三件是让传统祭祀变成现代纪念。
更是在呵护过往的记忆
有些人觉得,你们殡葬行业,不就是烧一烧、埋一埋吗?答案肯定不是这么简单。
有一年,我代表中国殡葬业参加全球殡葬大会,进行了5分钟的演讲。演讲后,有一个美国人现场提问:你是怎么理解信仰问题的?
这是一个足有3000人参加的大会,我又是中国殡葬行业的代表,所以我仔细想了一下,对他说: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通过我自己这么多年在殡葬行业的观察,我发现,我们的信仰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在教堂里。中国把清明节定为国定假日,它是一个祭奠祖先的节日,是除了春节之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些重要日子就包含我们的“信仰”。
全球殡葬大会共有4天的会期,在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那个美国人只要在会场或者其他场合看见我,都会远远地对着我鞠躬。
回到国内,我开始想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把殡葬做得太简化了?殡葬行业所做的,不仅仅是处理遗体,它更是在呵护过往的记忆、家庭的情感和社会的温度。所以,我们要把这一份事业提升到推进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高度去做。
向遗体捐献者致敬意
2002年,我们在全国创建了第一座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很多人问,你们一个墓园,为什么要建遗体捐献纪念碑?
这个念头,来自我不经意间听到的一件事。一个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家属向我讲起他家里的事情。他爸爸妈妈在生前签下了遗体捐献志愿书,可是当他父母离开之后,子女却不愿意兑现这个承诺。我问他是为什么。原来,捐献的遗体被送到医学院、用于给学生上解剖课后,就会集体送到火化场火化,而火化之后,家里人是收不到骨灰的。这样一来,每年清明节的时候,没有地方去扫墓,子女觉得有很多遗憾,所以不愿意兑现遗体捐献的承诺。
这件事让我挺受触动的。在走访了50个遗体捐献志愿者的家庭后,我们决定做这样三件事情:第一,为这个义举树碑立传。在这座遗体捐献者的纪念碑上,刻着上海每一位遗体捐赠者的名字;第二,在我们的推动下,医学院的学生在大体解剖前有了一个仪式——向大体致敬;第三,遗体解剖完之后,医学院会向捐赠者家属出具一张证明,这张证明上有全体师生的签名,表示对遗体捐赠者的崇高敬意。同时,还确定在每年的3月1日举行社会公祭活动。
我们觉得,墓地不仅是安葬逝者的地方,它也是一个能让我们纪念社会群体的地方。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每年只有两个遗体捐献实现者。到了今天,全国各地一共有30座遗体捐献纪念碑,上海每年的遗体捐献实现者超过2000人。这让我们觉得特别欣慰。
既要生死两安,更要生死两悦
我们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在和亲人告别的这一刻,领悟到向死而生的意义。因为只有悟透死亡,才能够了解生命的真谛。
曾经有一部日本电影《入殓师》,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影片中,一位大提琴手误打误撞成了一名入殓师。起初他对这个职业抱着排斥的心理,但后来逐渐热爱上了这个职业。借着这位新手入殓师的眼睛,电影通过呈现各种各样的死亡,展现了围绕在逝者周围的充满爱意的人们。
殡葬行业沉寂千年,因为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其难以改变,但是改变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一直对员工们说,我们今天做的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而是一个精神抚慰的事业。所以,2016年,福寿园创办了中国殡葬行业第一所学院,叫生命服务学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学院能够把死亡教育、生命文化、生命服务等理念更广泛地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我们来到墓地,送别亲人,不只是为了生死两安,更是为了生死两悦。生命的价值不是一路奔跑做加法,我们也要学会有能力去做一些减法。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不是物质层面,而是精神层面、情感层面。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死亡中读懂爱,感悟爱。
(内容整理自“造就”演讲)
终于,我又可以勇敢地面对死亡
纪慈恩
这件事曾经残酷地摧毁了我
到目前为止,我的生命被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之前和20岁之后。
19岁那一年,我最好的朋友得了肝癌。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真实地感受到死亡的存在。当时,她在荷兰留学。在荷兰,安乐死是一种合法的行为。因为已到肝癌晚期,病魔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疼得实在受不了,她甚至会咬自己的胳膊。所以,我去看她的时候,她求我为她签署安乐死同意书。
我那个时候太年轻,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承担得起对另外一个生命的责任。在万般无奈下,我狠心为她签署了一份安乐死同意书。
这个决定,由此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在她的追悼会上,当人们得知是我为她签署了安乐死同意书时,可怕的一幕出现了,我至今都无法忘怀。他们说,是我杀了她,他们说,我一定会得到报应。开始是一个人、两个人,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进行谴责。
在此之前,我每天都因为好友的去世而哭泣,用医生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人遇到这种事情时的正常反应;而自从追悼会后,我没有再对此说过一句话,我感觉自己已经无力面对这个世界。自我封闭,成了我保护自己的唯一方式。我每天都躲在屋子里,拉上窗帘,不和任何人打交道,也不和父母说话,只是每天坐在地上,问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那一年,我被确诊为“创伤后应激心理障碍”,是一种很严重的心理疾病。
经过一年半炼狱般的治疗,精神鉴定中心为我开具了一份已经康复的鉴定书,但实际上,我知道我并没有康复,因为我对死亡仍然有着非常深的恐惧。
死亡,它曾经这样无情而残酷地摧毁了我,我一定要认清楚它的真面目,我要看看它为什么会让我变成那个样子。所以,后来我做了一个决定,要去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临终关怀医院,去了解死亡的真相。
因此,我在21岁的时候,成了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
要清醒地活在当下
至今,作为一名临终关怀志愿者,我已经送走了几十位临终者。
我曾经以为,我是去与死亡对抗的,但没想到,最后我和它握手言和。
在临终关怀医院里,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死亡。有的人很平静地面对死亡这件事,有的人很挣扎、很折腾,也有的人活得很精彩。他们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走向死亡。
在我服务的对象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林的奶奶。她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太太,她常常对我说:“生命自有它的定数,我们要承认,生命就到这里了,我们就允许它到这里。”有很多次,她在深夜拉着我的手说:“如果有一天,在我生命的最后阶段,我意识不清楚了,我糊涂了,千万千万不要给我治疗,我不想看着我的血一点点变成黑色,我想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我发现有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大多数子女在父母病危或临终时都不愿意放手。后来,林奶奶的癌细胞扩散了,她的女儿一定要让她去做化疗,林奶奶不愿意,就用自残来抵抗。最后,她女儿看她这么坚决,才含泪不再逼林奶奶去做化疗。
在临终关怀医院,我听到很多家属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今天不给他治疗,我将来会后悔的。”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我们不能允许生命就这样轻易地终结,我们希望生命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可是事实上,生命终将会终结,这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渐渐明白,死亡有很多种维度,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非黑即白的,一定是绝望的、悲伤的。
我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天天和一群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活在一起,你是如何调节自己的悲伤情绪的?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想:为什么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就一定要有悲伤的情绪呢?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死亡是一件绝望而悲伤的事情。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死亡不再是让人恐惧的。
就像那位林奶奶,她之所以能够这样镇定而从容地面对死亡,是因为她已经深深领悟了生与死的意义。在临终关怀医院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其实取决于他活着的时候。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你可以好好地活,才能够好好地死,你只有清醒地活在当下,才能够勇敢地告别这个世界。
生命只有一次,但是我们曾经无数次地在影视作品中体验和直面死亡。对死亡的感知与体验,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活着。
我非常不赞成这个观点——好死不如赖活着。任何时候,无论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不会选择苟且地活着。
我认为我活着的意义就是:风风光光地来到这个世界,坦坦荡荡地活着;然后在我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有尊严地、安详地离开,不枉我曾经来过。
(内容整理自《青年中国说》和TEDx演讲)
更多资讯或合作欢迎关注中国经济网官方微信(名称:中国经济网,id:our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