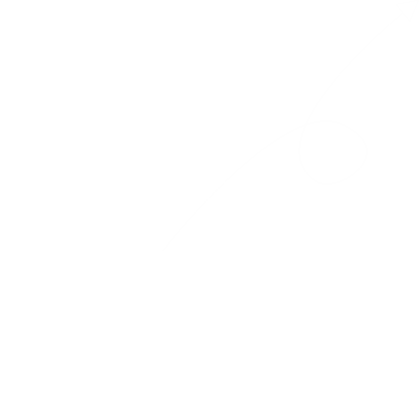嘉宾档案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讷河县。1983年,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专业本科毕业之后,奔赴新疆,在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4年至2001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获得硕士、博士学位。2001年开始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同时进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两年后出站。
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敦煌吐鲁番学。先后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敦煌民间结社研究》《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等多部著作出版。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200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和《唐高宗的真相》等课程,曾与著名作家阿城合作编剧大型电视连续剧《贞观之治》。
元宵节之称始于唐代,宋以后沿用不改。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元宵节最晚在唐代已经成为国家的法定节日。节日研究,最能发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特性,探索任何节日的来龙去脉,都会感到源头如迷雾深锁。而元宵节,又为中国文化之源远流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明。
一 多重渊源
最早记录元宵节内容的书籍是《荆楚岁时记》,作者宗懔,时间是555年。隋朝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作注,杜公瞻侄子杜台卿作《玉烛宝典》十二卷,保存了这些文字。
先看《荆楚岁时记》关于正月十五的记述: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
所记正月十五,分白天夜晚两个时段,所从事的活动不同,白天“祠门户”,晚上“迎紫姑”。从《荆楚岁时记》的记述看,当时节日活动,分白天、夜晚两个时段,白天“祠门户”,晚上“迎紫姑”。元宵节给后人印象更突出的是晚上的庆祝,但从《荆楚岁时记》中,还看不到类似的行动。迎紫姑,似乎是静悄悄的活动,看不到后来那样的灯火辉煌。
到了唐初,根据《艺文类聚》的记述,开始出现了夜晚观灯的内容。为什么会有“观灯”,后来的人们已经失去记忆,推测这一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说是来自汉代的“太一”祭祀,一说来自西域的佛教燃灯。后者,经常引用的经典是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元宵观灯的习俗来源,已经不能清楚说明,但隋炀帝留下一首《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 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灯火辉煌的夜晚,建筑了专门的设备,法轮、梵声无疑都是佛教的意向。这说明,至少隋朝已有正月十五夜晚观灯,而隋炀帝显然是从佛教视角看待这个观灯场景的。正月十五是道教的“上元日”,《旧唐书》记载,景龙四年(710)的“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开元天宝遗事》也记载:“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正月十五夜晚观灯,与道教或许也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如此一来,有关元宵节的来源探讨和描述,便形成了多源说。在讨论元宵节的来源时,学者强调重点各有不同,有热衷于一元说者,推测一种最早期的可能,然后否定其他的可能性。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节日,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发展的动力,其实就是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认同。
节日渊源的学术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即使早期的证据难以确凿,这本身就是社会习俗的特征:原来的涓涓细流早被遗忘了,当汇成大江大河时才发现探源的必要,而此时的源泉证据已经难觅踪迹。唐宋时期,所有关于元宵节的探源思考,都具有认同特征。这些探源文字,与其说是证据,不如说是同意表征。各家各派,都从自己认同的方向去探索源头,最终则形成了多元证明。探源研究当然是有价值的,虽然语焉不详,不过认同即承认,这是风俗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合法化”。
二 快速发展
元宵节最初是以地方节日的面貌呈现的。所谓节日,当然要符合岁时活动的特征,每年重复进行,内容相对稳定。南朝梁陈时期,已经存在正月十五晚“燃灯”的观灯之俗。
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录》,记载梁简文帝有《列灯赋》、 陈后主有《光璧殿遥咏灯山诗》,都是上元夜的背景,唐以前岁不常设,至宋初元游观之盛,冠于前朝。由此看来,在南北朝时期,元宵节主要是南方的节日,从梁朝、陈朝皇帝都有诗歌相咏的事实来看,最高当局已经参与到元宵节之中,说明此时已经脱离了民间的性质。作为地方风俗存在的元宵节,开始的脚步已经无从寻觅。《荆楚岁时记》标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这个节日已经进入文献的视野。而南朝皇帝们的作品,证明节日文化正在升级发展。
与此同时,北朝的正月十五,又有什么举动呢?《隋书》卷四〇《元胄传》:“尝正月十五日,上与近臣登高,时胄下直,上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曰:‘公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胜也。’赐宴极欢。”隋文帝与近臣登高,元胄没有参加,他正在“与外人登高”。皇帝特地请他来一起活动。正月十五登高,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活动。登高、宴饮,似乎是正月十五的传统内容。不过,到了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公开禁止正月十五的节庆活动。此事发端于御史台的副长官柳彧,他认为正月十五的“都邑百姓”庆祝活动,浪费财产,败坏风俗,建议取缔。隋文帝赞成并执行。其实,当时正月十五的百姓庆祝活动,并不局限于首都,柳彧的报告就提及“外州”。
如此看来,正月十五的节日活动,在隋朝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是内容方面,原来的登高、祭神等被戏剧汇演所替代,同时娱乐性代替了神圣性;二是规模扩大,全民性的节日氛围已经形成;三是进入长安,赢得长安百姓的欢迎。“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极其准确地成为全民性的素描。这为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此时的元宵节还属于民间节日范围之内,即使有高官显贵参加,还没有成为官方认可的国家节日。但元宵节在统一国家的首都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重视的一个发展要素。
不久以后,当隋炀帝执掌国家的时候,元宵节获得了皇帝大力推动。隋炀帝确切恢复正月十五的庆祝活动的时间并不清楚,但是《隋书·音乐志》的记载还是十分具体生动的:
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两京缯锦,为之中虚。三年,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以示之。(大业)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绣。其营费巨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十里外。弹弦擫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
前文说到“每岁正月”,之后分别提及三年与六年,那么三年之前只有元年、二年,而又有“每岁”这个概念,可以认为只有从元年开始才合适。元年自然是大业元年,即605年。观察这段文字,很明显,庆祝活动明确在晚上进行,这便是“从昏达旦”。万国来朝,应该是参加元日朝会的,为什么要留至十五日,似乎就是为了继续参加元宵的庆祝活动,“至晦而罢”,竟然进行了半月。
不仅如此,所记大业六年“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结合《炀帝本纪》,我们发现,竟然也是正月十五的故事:
六年春正月……丁丑(十五日),角抵大戏于端门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
又是一次连续半月的庆祝活动。如果仅仅是外交作秀,实在无法想象,一定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或者是借助长安已经日益成熟的节日庆祝实现一定的外交目的。史书强调隋炀帝的外交作秀,用意在于批判。其实,从节日的发展来看,正是这个时期,元宵节进入了成熟期。
如此,元宵节就从一个地方性、民间性的节日提升到了国家节日的高度。“自是每年以为常焉”,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从隋炀帝开始,元宵节的国家化正式起步,待到最后完成,还有一段路要走,直到唐玄宗时代来临。南北朝时期元宵节作为民间节日已经存在,在南朝甚至皇帝也参与其中。隋朝文帝时期,元宵节在长安已经拥有良好基础,并且发生明显的变化。文帝时虽然小有挫折,但到炀帝时期则获得巨大发展,而在统一国家首都的发展,为进一步的律令化打下深厚基础。
唐代皇帝似乎格外钟情于元宵节。中宗、睿宗和玄宗都是其中的代表。《大唐新语》是如此记载的: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风光正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燃。”文多不尽载。
中宗时期如此,睿宗时期也毫不逊色。《朝野佥载》记载:
睿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乐之极,未始有之。
这已经是十分热闹的景象了。到了玄宗时代,正月十五的活动皇帝依然兴趣盎然。《明皇杂录》载玄宗“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
皇帝的热衷,最重要的意义是显示了节日的影响力,如果隋炀帝利用元宵节有加强外交工作的含义,那么到玄宗时代,更多的是与民同乐。参与节日的社会人群众多,从一般百姓到王公大臣、文人雅士、居民士女都是积极热情的投入者,而皇帝的参与,自然是顺应了民心的行动。何况,皇帝及其身边人,也有娱乐的需求与愿望,又有与民同乐的良好理由,何乐而不为。
元宵节成为国家的法定节日,就是在玄宗时期确立下来的。何以证明这便是法定假日的出现?唐代国家法定假日,有“假宁令”规定,《唐六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条对此有所记录,正月十五是一天假期。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把这个内容标示为“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年”,意为从七年到二十五年唐令都是这个内容。敦煌文书P.2504《唐天宝年代国祭、诸令式等表》,其中的假宁令内容,与《唐六典》一致,正月十五也是放假一日。敦煌文书S.6537v《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记录了三元日的假期情况,写作“右件上中准令格各休假三日,下元日,休假一日”。这说明,天宝三载(744)的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燃灯放假,后来修订为正式的法律形式。这其实就是“永以为例程”的含义。根据《天圣令》,到了宋朝,正月十五放假三日。但是,就在唐玄宗时期,正月十五已经升为三天假期。由此可知,宋代的元宵三日假期,是继承唐朝的。
据《唐会要》天宝三载十一月敕:“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旧唐书》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多出一个发布日期。玄宗于天宝三载十一月“癸丑,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永以为常式”。两书中都有“依旧”一词,让人感觉到此前已经是三天假期,但是没有成为“常式”,而这次从法律上确定了三日假期的地位。
唐朝的法律即律令格式。法令,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法令的承认就是国家的正式承认。正月十五的节日活动,早期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大约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地方节日,长安的正月十五节日活动,应该是受到外地影响,就时间而论,根据隋朝柳彧的说法是“近代以来”。正月十五作为节日,来自民间与社会的推动是主要的,相对而言,朝廷与皇帝的加入是滞后的,但是他们为其作为国家节日的升级却发挥着关键作用。长安因此变得很重要,没有长安民众的欢迎,就很难获得国家主政者的关注,没有这些政治上有能量的人群的支持,就不可能国家化,不可能给予法律地位。用“令”的方式规定国家节日,节日因此成为国家行为,这既可以称作“律令化”,也可以称作“国家化”,是研究古代节日文化的重要方面。
三 社会狂欢
唐代元宵节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动,尤其是朝廷和皇帝们表现出来的积极性,极大地提高了元宵节的地位,而通过唐令确定元宵节为国家节日,作为国家行为的元宵节获得了空前发展。古代中国重视法规建设,而到唐玄宗时代,制礼作乐进入高潮,从《唐六典》到《大唐开元礼》甚至包括《开元释教录》等著作都完成于开元时期,都是朝廷系统努力的结果。把传统的民间节日“律令化”,变民间传统为国家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国家引导风俗的努力,而后世对这些节日的继承证明,唐朝的制度化获得了后世的承认和继承。
就唐代的元宵节而言,已经有研究者使用狂欢来形容,其狂欢特性值得重视。狂欢的社会价值是尽情娱乐与放松,对于任何社会生活而言,作为张弛有度的一部分,狂欢节日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社会狂欢节日,需要具备几个基本要素。试述如下:
第一,全民性。对于狂欢节日而言,必须获得社会各个阶层和人群的认同,认同率越高,狂欢的社会热情越高,狂欢节越成功。隋唐以来的元宵节资料,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长安城,元宵节受到了极大欢迎。《隋书·音乐志》所载隋炀帝时的元宵节情景很宏大热烈,虽然笔法是批判的,但反映了一定实际情况。柳彧的反对报告,是更尖锐的批评,但同时也显露出当时的全民性:“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从整个家庭,到全社会,都热情拥抱这个盛大的娱乐节日。
唐朝继承隋朝传统,长安的元宵节继续在娱乐方向发展,而其全民性参与的特点有增无减。《大唐新语》所记与大业时期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从王主之家(亲王公主)、贵戚之属,到“下隶工贾”,“无不夜游”,全民参与得十分充分。中宗皇帝看来是特别热衷元宵节的,他自己不仅微服出宫观灯,当夜还“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者”。应当是宫内之人抵挡不住节日的诱惑,皇帝皇后既然也要微服观灯,允许宫女前往观灯就成了一种临时的福利。后来,不得已只好宫中大搞活动,用以抵御宫外的诱惑。
有关元宵节的渊源,前文所述,最后形成了多元认识。所有人群都认为元宵节与自己有关,这是全民性认同的基础。这在节日实践过程中,自然有利于全民性的参与。设想,有部分社会人群认为某节日与自己无关,他们的参与热情必然会受到压制。
第二,娱乐性。娱乐作为人群生活,需要是绝对的,不论贵贱高低,凡社会人群都是一样。所以,节日必须具备娱乐性,才会获得社会各阶层和人群的欢迎与参与。从隋朝开始,元宵节的娱乐性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传统中的与祭神相关的“神圣性”则渐渐褪色。神圣性多与禁忌相伴随,而与娱乐相违背。唐玄宗从开元后期始,时常由政府出资努力推动官员和长安的娱乐活动,促成官员们的游乐活动。而元宵节获得国家法律的认可,尤其是拥有特定假日,这就为元宵节的娱乐活动提供了重要条件。现在可以看到的唐代文字记载,元宵节的核心内容就是娱乐,神圣禁忌、政治纪律、道德教化,等等,在元宵节的狂欢中,一切为娱乐让路。
第三,丰富性。唐代尤其是都城长安的元宵节,所持续的时间尚不确定。如果从隋朝的记载来看,正月十五不过是起点,庆祝活动常常进行到月末。唐代元宵节,最初是一日假,从天宝三载之后,扩大到三日假,那么狂欢活动就有了连续三日进行的条件。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玄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五、十六日,在京师安福门外安装二十丈的灯轮,“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相应地一定有假日伴随,即使没有律令根据,肯定有皇帝的临时敕书。不管是一天还是三天,狂欢活动必须有足够多的内容,否则没有办法填满假日。元宵节,给人印象最深的通常是燃灯,先天二年玄宗的巨大灯轮竟然燃放五万盏灯。因为元宵节燃灯事项最突出,后来也称元宵节为灯节。
灯下踏歌,是同时开展的娱乐活动。踏歌类似集体舞,对于营造节日气氛最有帮助,而多人参与的大型项目,也让节日更具狂欢色彩。
戏剧展演。从隋朝开始,在元宵节进行戏剧演出就成为惯例,每到正月十五,“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隋书·长孙平传》所谓“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鍪甲之象”,证明戏剧颇能反映生活,因为不能穿上真正的盔甲,只好在衣服上画上盔甲,然后扮演相关剧中人物。当时的戏剧,为使剧情逼真,相应的道具使用已然很普遍。戏剧因有剧情,是最有条件占据观众时间的项目。
当然,还包括丰富多彩的食物供应,这是任何节日都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
第四,释放性。唐朝依然坚持古老的宵禁制度,生活在长安的人,很少能见到长安夜景,这事实上构成了日复一日的长期禁锢。而元宵节给长安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可以在正月十五的夜晚突破禁区,一整年的夜晚被禁锢的身体与精神,在这一夜彻底释放。唐玄宗的朝廷命令“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开坊市,即是临时取缔宵禁。苏味道《正月十五夜》“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反映的同样的宵禁取消。元宵节狂欢,正因为对应一整年的宵禁制度,具有解放的意义,社会释放性心理得到满足。长期压抑之后的短时间情绪宣泄,引发社会兴奋度爆炸,元宵节于是成为狂欢节。
其实,包括元宵节在内的唐代法定节日,都多少带有娱乐化的倾向,对于整个社会文化而言,节日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是健康的,具有必然性。
更多资讯或合作欢迎关注中国经济网官方微信(名称:中国经济网,id:our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