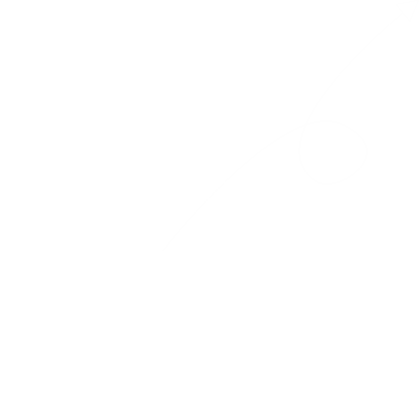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散文的主流是文化大散文。这种散文,大量涉足历史的后花园,力图通过对旧文化、旧人物的缅怀和追思,建立起一种豪放的、有史学力度的、比较大气的新散文路径。应该说,这种散文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改变了当代散文的一些面貌,但也存在着一个普遍而深刻的匮乏——那些本应是背景的史料,因着作者的转述,反而成了文章的主体,自由心性的抒发和心灵力度的展示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当散文一再地被历史史料和文化感慨所捕获,带着个人发现的“记述”反而成了稀有的品质。在这个背景里,我更愿意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所谓“向下”的写作,就是一种重新解放作家的感知系统的写作,使作家再次学会看,学会听,学会闻,学会嗅,学会感受,和生活的现场、大地的细节、故土的记忆重新建立联系。而当散文重新回归具体、细小、卑微、密实之时,相应的问题亦随之而来:散文这一似乎没有门槛的“轻”文体,该如何抵达精神思想的宏阔深邃呢?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散文易学而难工”(王国维语)。因着散文是亲切、平实和透明的文体,话语的姿态放得很低,结果,那些轻飘的感悟、流水账般的记述、枯燥的公文写作、陈旧的风物描写、堆砌的历史资料,都被算作是散文了,这在当下的散文写作现场里俯拾即是。并且,只要和文学沾边的人,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是不会写散文的,但承认自己不会写诗的人则不在少数——在多数人眼中,散文实在是太容易写了。
这种“太容易”所造成的散文数量的庞大,究竟是散文的幸还是不幸?我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但我一直认为,散文当然可以有轻逸的笔触,但散文在骨子里应该是重的。它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情与思,越重,就越能打动读者,越能呈现经验和事实的力量。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自1992年以来,他每年都花12至16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惟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象),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甚至一些散文,如我所推崇的台湾作家陈冠学的《大地的事》,它看起来只是关乎田园琐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事或许是轻的,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
正是因为这样的散文让我们摸到了作者的“心”,有了“心”这个隐秘的维度,它的精神空间才变得宽广和深刻。而当代的散文,普遍的困境就是只有单一的维度,它的轻,就在于单一,除了现实(事实和经验)这一面,不能给读者提供任何新的想象。在一个散文写作日益泛滥的时代,重新亲近一种“向下”的写作,重申写作的生命维度,才能使看似“轻”的散文成为发人深省的“重”。
(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