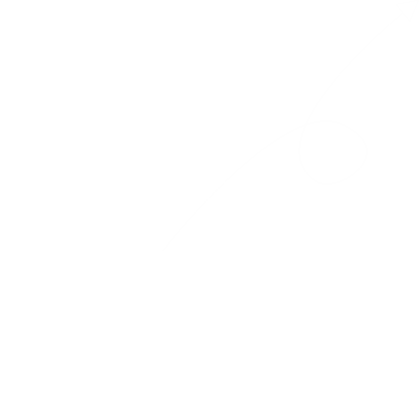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人们在柯桥区参观经典印染花型设计。近年来,有“中国最大染缸”之称的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借助创意设计平台,充实印染业设计力量,推动纺织印染产业升级。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本报记者刘荒、张典标
工厂搬迁与否,早搬还是晚搬?这个曾令赵国平辗转反侧的难题,如今早已有了答案。但若叫他重新选择,照样还会犹豫再三。
早在2010年,这位绍兴柯桥先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与众多本地印染企业同行一样,陷入这个由产业集聚升级带来的难题。
按照当地政府“绿色高端、世界领先”的产业定位,这些印染企业的“前途”,从此指向30公里外的滨海工业区。
“去”就要升级,“留”也得转型,赵国平与大多数卡在中间的企业主一样,迟迟拿不定主意。
柯桥由原绍兴县撤县设区而来,在全国印染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素有“中国最大染缸”之称。以至于人们用浸染布料的染缸,泛指这里的纺织印染业。“染缸”也成了柯桥的代名词。
这样一直拖到2015年,柯桥区发起第三批产业集聚行动:明确除滨海工业区外,其他地方不再保留印染企业。
深陷焦虑之中的赵国平,终于下决心转战滨海工业区,做出“从业20年来最艰难的一次抉择”。
如今经过集聚升级,当地印染企业已由212家减少至109家。
这个自带色彩的“染缸”故事,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叙事主题:赵国平们“何去何从”的纠结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与简单盲目的政策“一刀切”相比,这种让市场主体“走投有路”的做法,又如何廓清政府的职能……
本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两度走进柯桥,寻找答案。
染缸的颜色:坯布知道,江河也知道
“世界纺织看中国,中国纺织看柯桥。”这座纺织传统深厚的千年古镇,早在明清时期就有“时闻机杼声,日出万丈绸”的盛誉。
改革开放之初,柯桥人瞅准涤纶面料热销的机会,率先办起纺织印染厂。时至今日,一些老柯桥人仍管织布叫“跳迪斯(涤丝)科”。
1979年,赵国平的父亲赵源龙带领村民办起了纺织印染厂,成为第一批“跳迪斯科”的柯桥人。一时间,生产绦纶、丝绸等纺织品的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景象。
柯桥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河网密布,一批头戴乌毡帽、手摇乌篷船的布贩子,沿河叫卖这些村办工厂生产的布料,自发形成一条热闹的“水上布街”,全国各地布商纷纷涌来进货。
由于市场面料种类多、花色新,生意越做越红火。这些人称“船老大”的布贩子们抛橹上岸,从“布匹一条街”到“中国轻纺城”,亲历了这个世界最大的轻纺集散中心诞生。
上承织造下接服装的柯桥印染,始终与轻纺市场繁荣相得益彰。
据柯桥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原副局长徐祥林介绍,“染缸”撑起柯桥工业经济的65%,占全国纺织印染总量的三分之一。产量最高的年份,全区染布超过180亿米,可绕地球450圈。
多年来,在这些异彩纷呈的染缸背后,是柯桥人再熟悉不过的画面:进出柯桥城区的公路上,运送各种布料的大货车终日川流不息,拉进来的成匹的白色坯布,运走时都变成五颜六色的印染布。
然而,印染与污染仅一字之差。近年来,人们逐渐发现这些染过坯布的染料,也污了江河,涂了田野。
“前些年,印染厂染什么布,一看河水就知道了。河水跟着染料变,染黄布就是黄河,染绿布就是绿河。老百姓都叫它们‘彩虹河’。”陪同记者采访的当地人魏金金回忆说。
柯桥地势平缓,河道流速慢,自净能力弱。一些印染厂取水、排水的河道,也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水源。在当地工业污水排放中,印染业占比曾高达90%;与水相关的环保投诉,一度占到六成以上。
在坯布印染过程中,每天还产生约2000吨废渣。过去曾有个别企业图省事,将这种染料和污水残渣倒进农田,惹得老百姓抱怨不断。
柯桥人腰包鼓了,对环境也有了更高期待。上世纪90年代,柯桥修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60万吨。然而,随着印染产能不断扩大,个别企业偷排偷放,排污管道泄漏等现象仍时有发生……
前些年,印染业利润之低,令人大跌眼镜。2009年,柯桥染布156亿米,利润只有13亿元,平均每米仅挣8分钱、耗水达12.7公斤。依此推算,一年就得抽干20个西湖,而每吨污水又要污染20吨水体。
尽管市场始终在竞争变化之中,行业利润也会发生波动,但如此巨大的环境代价,实属难以承受之重。国内产能过剩和全球产业转移,对柯桥印染业的冲击和影响也日益明显。
“现在不光西南地区,其他沿海省份也在搞印染。”浙江省印染行业协会会长、绍兴海通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传海直言,印染行业属于限制发展的“两高”产业,各地扎堆入局势必加剧产能过剩。
早在2002年,为突破工业发展空间限制,原绍兴县提出在滨海工业区“再造一个绍兴”。被寄予厚望的柯桥印染行业,开始了产业集聚的“破冰之旅”。
据柯桥印染产业集聚升级工程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集聚办)首任主任赵金良介绍,当时只招来52家印染企业,由于园区未达招商预期,被迫引进其他产业入驻,形成不同产业“杂居”的格局。
2010年,原绍兴县决定5年内将八成以上印染企业迁至滨海,在毗邻钱塘江入海口的滩涂上,规划出一万亩土地承接集聚。
前来考察的印染企业老板们,刚看到这片荒无人烟的土地时,心里直打怵。
企业的脸色:“小账”算清,还得“大账”算对
显而易见,柯桥印染产业集聚的目的是升级,并非简单的搬迁。
与市场自发形成的集聚不同,这种由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更需要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集聚办在对100多家印染企业筛选摸排前,本想先抓大放小“打个样”,没料到只有23家老板点了头。
“大多数老板都在观望,指望别人先蹚路,自己再去也不迟。”赵金良回忆说。
根据产业升级的目标,他们对这些印染企业生产规模、工艺设备和环保水平,设立了相应的进入门槛。摆在企业面前只有两条路,达标者可搬迁升级,未达标和退出者,只能选择合并、转型或关停。
按着集聚企业标准,印染企业日均污水排放量为2000吨,可获批工业用地50亩。排污量每超过1000吨,可增加10亩土地;排污量不足的,可与其他企业合并达标后入驻。
“政府只给一块地,厂房由企业自建,升级还得增加投资,最终效益仍是未知数!”一些印染企业老板担心经营成本偏高,将来竞争不过外面的印染企业,甚至还有过“谁先集聚谁先死”的说法。
从1995年接手父亲创办的印染厂后,赵国平搞得有声有色——这座占地百亩的工厂,年产值达2亿元,利润至少2000万元以上。守着还算滋润的小日子,他感觉实在没必要再花钱瞎折腾。
“员工都是邻里乡亲,谁愿意舍近求远跑通勤?”最初并没动过搬厂念头的赵国平,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
赵金良的回忆,也间接证实了这种说法。“摸排时企业反映,员工嫌远不愿意去,新厂重新招人工资得比原来高,短途运输成本也会增加。”当时按赵金良测算,企业经营成本将增加20%。
李传海以集聚企业“煤改气”为例,向记者解释道:“不仅经营成本激增,还需要购买新设备替代原有燃煤设备,这又是一大笔开支。”
在绍兴柯桥恒惠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惠),总经理金良指着一套日处理污水2000吨的设备告诉记者,2011年他们花1000万元,购买这套本地最早的膜处理污水系统。
本来打算使用10到20年,光钢板就用了400吨,现在根本没法拆走了。
更让人心里没底的是配套。当时,现场“三通一平”还没搞,政府只承诺会同步建设电厂、污水和污泥处理厂等配套设施。万一这些配套设施跟不上,搬迁过来的企业连生存都成问题。
事后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直到2015年,有的重要配套设施才到位。一位知情人透露,园区曾因用地指标不足,延误建设一年多。
这段时间,有人患得患失,有人中途反悔,还有人无可奈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老板抱怨,“我们有排污牌照,为啥非搬不可呢?”
一些负有就业和税收责任的镇街干部,在落实集聚动员任务时,也存在口气坚决而态度暧昧的情形。
果然,第一批集聚虽小有收获,却并不乐观。3个月后,他们又启动了第二批,两批一共签约不过40家企业。第三批集聚攻坚时,仍有100多家印染企业在观望中。
产业集聚对原有配套企业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装机容量3.9万千瓦的上游的热电厂——绍兴其其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其其热电),高峰时年销售额两亿多,供热收入占了大头。
其其热电总经理叶利其坦言,供热失去下游印染厂的出口,按照要求电厂也不能发电,而滨海已有配套热电厂,我们又跟不过去。
热电厂关停后,当地政府根据装机容量和煤价,补偿3年利润。叶利其说,热电厂属于特殊厂房,只能拆除,无法改做他用,其处理和补偿方案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政府的角色:“走”有路,“投”也有路
“我们特别担心,先来的企业活不好,后面就更不敢来了。”干了五年半集聚办主任的赵金良,苦辣酸甜尝了个遍,“上有集聚指标,下有企业诉求,夹在中间压力非常大,搞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为了减少企业后顾之忧,他们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如鼓励印染企业加大设备更新改造,对技改给予一次性补贴15%,高于普通行业15倍。
同时,禁止没有排污指标权的企业生产,支持由政府核定的排污指标入市交易,也可抵押贷款。
坊间传言,当年有的企业玩“猫腻”,重复回注排放污水虚增排污量。一些受访企业老板不以为然,反问造假哪有这么容易。
“排污指标开始几百元一吨,没多久就涨到几万块钱。”李传海回忆道。
柯桥还给集聚企业两年过渡期,老厂不关、新厂照开,排污量不超标即可。过渡期结束,老厂土地可“退二进三”,由工业用地转为商业开发。
还有受访企业老板向记者反映,第二、三批企业老厂房的处置政策,目前执行还不到位,耽误企业退出和转型。
李传海等人认为,老厂转商业开发和排污指标可交易抵押,是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最核心的两条政策,为不愿或无力集聚的企业留了退路。
在让企业“走投有路”的同时,环保的“紧箍咒”也越念越紧。第二批排污量门槛翻番到4000吨,按60亩标准供地;第三批排污量门槛拉升至1万吨,按80亩标准供地,并明确要求除滨海工业区外,其他地方原则上不再保留印染企业。
时过境迁,当人们意识到“这回政府是来真的”时,集聚条件也已今非昔比了。“第一批土地价格每亩才2万元,如今已经涨了10倍。厂房每平方米的建设成本,也从800元升至2000多元。”有人不无懊悔地说。
“对小企业来说,这样不大公平。”一位受访印染企业负责人吐槽,“我们都是合法企业,区别不过大小而已,生存还是淘汰,最好由市场来决定。”
再三权衡的赵国平,最终选择与另外一家印染企业合并,总算凑够一万吨污水排放量,赶上第三批集聚的“末班车”。
2018年5月,总投资7亿元的禾盛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投产。赵国平与合并企业老总一道,定期出任公司轮值董事长。
感慨之余,赵国平并不回避老厂土地升值的话题。两相比较,他感觉并未吃亏,毕竟有老厂土地在手,将来转型发展也有本钱。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照样还会纠结的!”他回答道。
随着园区准入门槛持续提升,企业合并力度不断加大。第一批21家集聚企业,股东来自23家企业;第二批19家涉及28家企业;第三批17家涉及63家企业。加上2002年入驻的52家,目前柯桥共有印染企业109家。
恒惠自有1000吨排污指标,也考虑过“组团”合并,花费大半年时间也没谈拢。后来,他们把印染车间搬至上虞区一处化工园内,与滨海工业区仅一江之隔,相比搬迁的费用略低一些。
也有一些企业选择退出,将排污指标转卖。
2016年,原绍兴华纺染整有限公司负责人何云来,刚以每吨1.8万元价格卖掉600吨排污指标,价格就涨到了2.4万元。后来,他儿子和小舅子又想干印染,只得合伙从别处买排污指标了。
“现在有钱也买不着!”退休在家的何云来对记者说,“己经停产的老厂房,每年租金也从40万元涨到100多万元了。”
16岁就在市场卖布的傅双利,从内销做到外贸,2008年出口额达3500万美元。他通过购买原绍兴迎丰纺织有限公司的排污指标,2011年终于入局印染,补全了卖布、织布和染布整条纺织供应链。
也有个别印染企业转而当上“包租婆”:靠出租土地、厂房或者设备盈利。“有的直接出租厂房,有的承租企业租地自建,租金最高的是连厂房带设备一块出租。”
市场的本色:尊重规则,更要直面竞争
在柯海大道旁的浙江鸿大印染集团(以下简称鸿大)建筑工地,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鸿大项目筹建办主任孙伟良讲述了一段“退群风波”的“家史”。
2018年,绍兴市启动滨海工业区第四批集聚项目,要求越城区47家印染企业合并成5家,跨区域集聚至滨海工业区。
目前拥有2.6万多吨排污指标的鸿大,号称浙江规模最大的印染企业,由16家印染企业发起成立。
“中途有两家公司股东退出,包括一家牵头的大股东”,孙伟良解释说,“这些股东企业排污指标不同,决策份量自然有别,加上前期磨合运作不畅,一些小股东感觉没有存在感,甚至心生退意。”
经相关部门协调沟通,最终这家大股东决定退出。这时已无其可供选择的企业合并,此举意味着这家企业或将彻底退出印染行业。
小到车间分配、活动组织、会务协调,大到法人治理结构、财务、融资方式等事项,一直扮演协调角色的孙伟良,着实付出很大气力,也受了不少委屈。
据初步测算,鸿大正式投产后,年产值约50亿元,纳税10亿元,尤其每年水、电、气等费用,较集聚前可节省8000万元左右。
这种因市场准入门槛限制而“自愿”合并的企业,内部组织、管理机制存在先天性缺陷。虽说共同成立了新的企业,股东们却依旧各干各的,只是把原来的企业变成车间了。
深谙其中难处的徐祥林举例说:“如果投资一个数亿元的大项目,是选择自有资金还是银行贷款?拿不出现金的股东会希望由集团公司贷款,而这对于现金充足的股东来说,则意味着增加财务风险。”
经历过“退群风波”后,鸿大制定出权责明确的决策机制:遇事集体商议,有争议时少数服从多数。说来有趣,虽然企业前期运作出现问题,当地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不减,光项目动工剪彩就搞了四次。
不光企业内部要磨合,配套产业也要对话。滨海工业区有4家配套热电厂,在为印染企业供热的蒸汽价格上,供需双方经常争论不休,意见难以统一。
“在相对垄断的电厂面前,印染企业成了弱势群体。”柯桥区印染工业协会秘书长王建平还打比喻说,“蒸汽每个月涨二三十元。一年下来有的企业得多花2000多万元。”
柯桥区印染工业协会和柯桥区热电协会,都曾代表各自行业“出头”,为蒸汽定价方案“斗法”。
他们向相关部门反映各自诉求,由物价局主导谈判,最终双方就定价方案达成共识——在成本基础上,给电厂5个点的固定利润,煤价一有变动,蒸汽价格也跟着调。
在浙江越新印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新)董事长濮坚锋看来,企业合并后的磨合、要素价格的波动,都属于不可避免的短期阵痛。
随着产业集聚人才竞争加剧,核心人员频繁流动现象令人烦恼,但他坚持认为,集聚形成的区位优势会带来长期机会,与企业设备技术升级同步,管理模式也可以做一些创新尝试。
在越新一楼的数据中心,一块蓝色大屏幕上,分区显示订单排产、订单进度、订单结构、业绩分析等指标。
濮坚锋不无自豪地说:“这两年我们搞数字化改造,已实现生产的智能监控、智能排产和质量分析。”
“这套系统相当于现实工厂的数字孪生。”他进一步解释说,通过从每一台机器上采集的数据,可以追溯生产操作流程中每一个环节,不断优化生产流程,实现管理的自动化和数字化。
同样在数字经济赛道上奔跑的,还有浙江迎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去年在上交所成功上市的印染企业,被誉为“染缸”里飞出的“金凤凰”。
董事长傅双利在刚刚装修的新厂房里,兴致勃勃地介绍自主开发的“产业大脑”,客户通过手机可以看到企业生产流程和质检标准,从而打通生产端和消费端。
目前,当地有40余家印染企业正在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徐祥林告诉记者,柯桥产业集聚升级以来,累计腾退土地1.3万亩,淘汰落后设备2000多台,高端设备普及率60%以上,已有一批传统印染企业采用数码印染、无水印染等创新型、生态型的印染工艺。
与此同时,每米印染布附加值提高15%以上,平均浴比由1:10提高到1:5,即原本染一米布需要10公斤水的话,现在只需要5公斤。“废水废气减少排放1/3,土地节约了1/3。”他补充说。
集聚终将尘埃落定,升级绝非一劳永逸。这些通过集聚升级“关隘”的印染企业,仍然感到压力不减。
无论是去年秋季短暂的拉闸限电,还是“每年削减3%-5%的排污指标”“实行排名后5位的末位淘汰制”业内传闻,让这些印染企业老板愈加清醒,在尊重规则的同时,更要勇于直面竞争。
归根结底,市场主体的竞争实力,一定来自于市场。
更多资讯或合作欢迎关注中国经济网官方微信(名称:中国经济网,id:ourc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