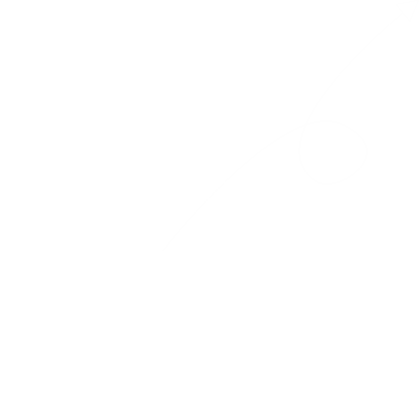我国城市发展70年来,已从解放初期以乡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发展至今日以城市为主体的工业社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规模及城市数量等发展规模比肩发达国家,其辉煌历程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红利所成就。改革开放和工业化为制度红利的释放和放大提供了原动力,城乡关系的制度规定性则是制度红利所基于的资产原值。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国城市发展再出发,需要遵循创新体制,融合城乡的必然导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是根据中国的国情而制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基础薄弱,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生产力低下,而人口众多,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体系构建,土地公有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层级制度则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全方位推进的保障。城市发展需要空间作为载体,在土地公有制下,土地征用不是一种市场交易,而是一种行政需要,土地征用时相对简单的法律程序,低廉的获取成本使操作实施得以高屋建瓴;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人口从农村到城市单向流动,城市人口有序扩张,同时农村优质的人力资本通过考学、征兵等途径进入城市,不仅为城市发展积累了高素质人力资本,也有效地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贫民窟”现象;权限激励的层级制度规定城市层级越高,城市发展的权限和资源调动能力越大,集中力量办大事,客观上促进了资源的聚集,产生辐射拉动和资源虹吸的双重效应,其影响程度和范围随行政层级的提高而扩大。
中国城市发展制度红利的释放需要原动力,主要表现在工业化的拉动和改革开放的放大效应。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援助中国156个大的工业化项目,不仅造就了中国工业体系的基础,还带动了新城的发展。除此之外,沿海城市“三来一补”模式同样通过工业化的拉动激发了城市发展活力。
改革开放前城市化进程缓慢,制度红利释放的速率和效应低。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不断宽松,城市的居民数量增加,同时对外开放带来的资金、技术、海外市场、城市发展理念,使得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层级制度的城市发展红利得以放大实现。从制度红利释放的速率和效应看,城市发展70年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49年至1978年,此时期以重工业化为导向,城市数量和规模扩张速度较快,但劳动就业容量小,城市化速率提升缓慢,而且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人口容量也相对有限。第二阶段可细分为1979年至1999年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和2000年至2011年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城市服务业就业容量大,户籍制度松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成为城市发展的制度红利来源,城市化每年保持1.2个百分点的提升速度。在第三阶段,户籍制度的红利日渐式微,土地制度的红利空间也不断减小,但行政层级制度红利趋于放大,行政层级高的特大城市、大城市在城市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明显优于层级较低、规模较小的城市,城市发展出现大城市化趋势。
红利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有资本,城市发展的资产原值在于城乡关系的制度规定性,规定性就在于城乡关系属于以农补工。第一,从农业与工业看,改革开放前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将农业生产的剩余全部转移到城市发展工业。改革开放后,取消农业税,但农业的比较收益仍低于工业,处于竞争劣势地位。第二,从农民和市民二元户籍关系看,户籍制度保留单向通道,将农业户籍中的优质人力资本流向城市。第三,生态环境容量资产的升值,是从农村集体土地到城市工业和商住用地的单向流动,而生态环境容量资产的使用,则至少是城乡共享,甚至是城市、工业污染物的吸纳场所。因此,城市发展的制度红利,成就了新中国辉煌的城市发展进程,但从某种角度看,农业、农民和农村作为制度的资本,没有获得应有的补偿,红利分配不对称。
制度红利铺就了城市发展的快捷通道,但在社会进入城市主体后,制度红利日渐趋薄。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互联网的普及和生态空间作为生活品质的内容日益受到重视。社会服务的均等化和社会管理的扁平化,使得城市的优势亦日趋弱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发展走向高质量,推动城乡一体发展,需要再认识和更多的思考。应推动城乡融通和双向流动,乡村非农用地可以入市,城市资本可以下乡。城市居民不仅可以携带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下乡,投资商、企业家也可以到乡村创业。更重要的是,应大力推动城乡均衡发展。当前,城市发展已有相应的制度性安排,但还需要进行结构性转变,城乡社会公共服务应缩小差异,城市的优质资源配置如教育、医疗等,不应该局限在行政层级高的城市,居民选择城或乡,应是个人偏好,而非刚性需求。因此,展望未来的城市发展,应是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新格局。(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 潘家华)